第十二届中国摄影年度排行榜丨马良:永无岛

马 良
毕业于上海华山美术学校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。2003年开始艺术创作,在世界各地举办个人作品展50余场,参与重要的摄影及当代艺术群展百余场。作品被众多美术馆和机构收藏。
2012年完成摄影代表作:公共艺术项目《移动照相馆》。2017年下半年,从戏剧创作领域回到摄影创作领域,继续用影像媒介进行创作。2023年挪威白菜出版社出版作品集《镜中人、景中人》,获得挪威最美的书奖。202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个人作品集《永无岛》,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摄影文化史文集《失焦记》。
评论文章
惘然之梦
文 / 黄天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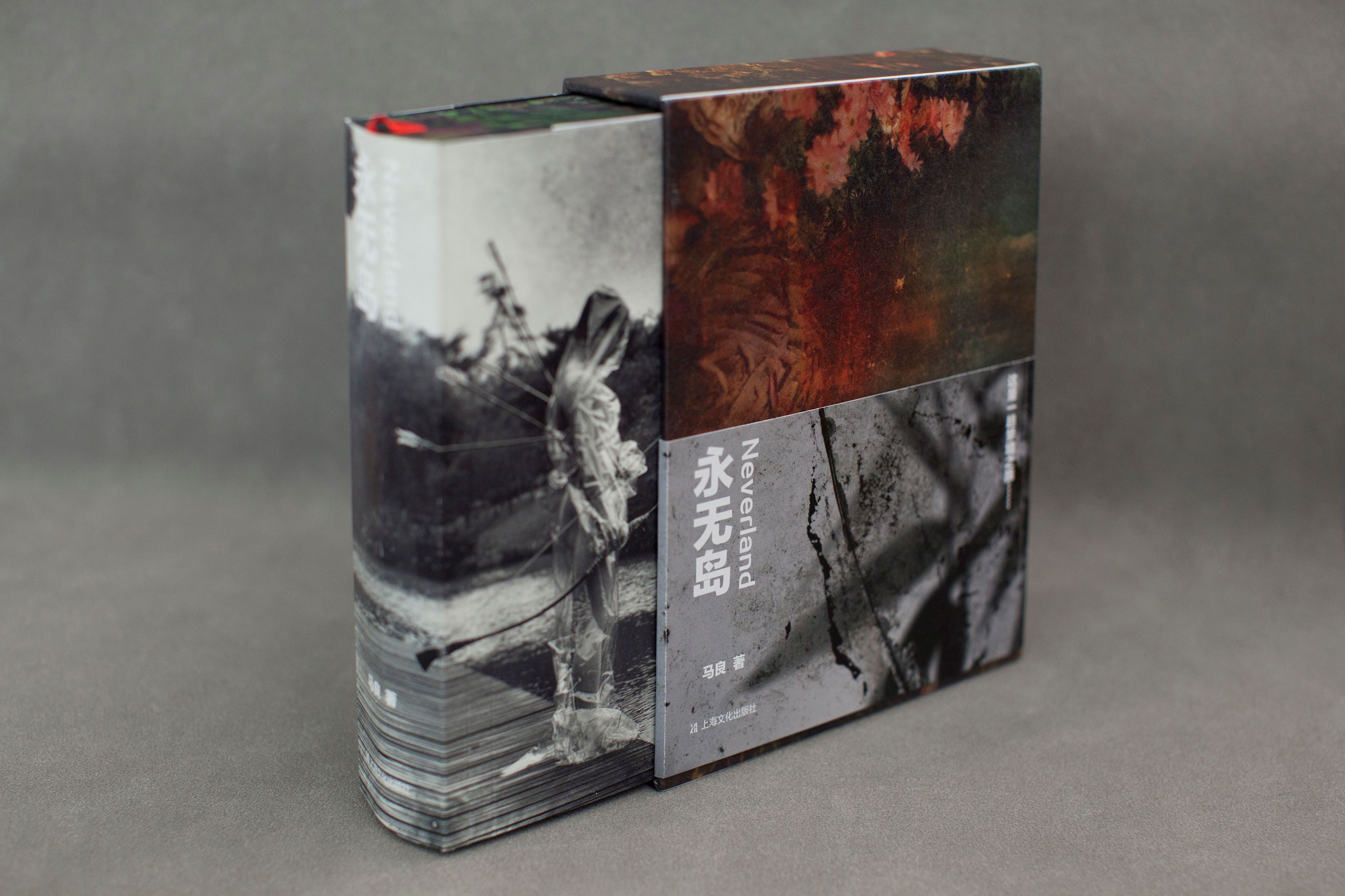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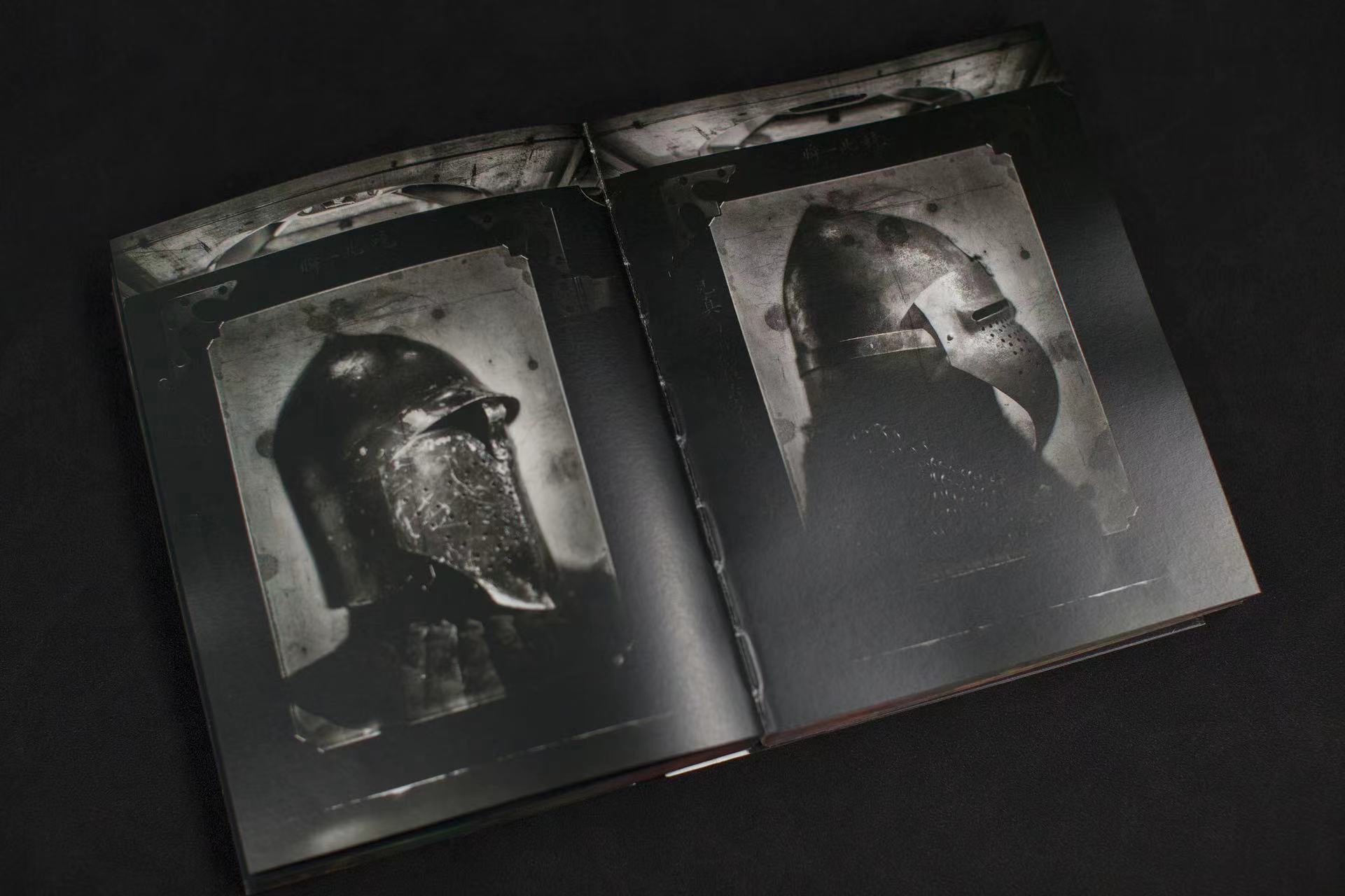
《永无岛》,2024
在马良的作品里,我能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渴望。
他不确定岛屿是否存在,却笃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;他悲观地认为过去无法重现,却执拗地一次又一次不断尝试。在用画面构成问句,不断追问的过程中,他毫不掩饰地袒露着内心最私人的情感,邀请作为观者的我们一同乘上小圆舟,踏上这趟也许没有答案的永无岛追寻之旅。
这也是一趟梦境之旅。
马良作品中的“戏剧性”也许是他最为鲜明的特色,他的每部作品都像是在演出戛然而止的故事:戴着面具的少年聚集在废弃的乐园中(《不可饶恕的孩子》)、发霉的浴室里少女制造出的棉花糖巨大而甜蜜(《棉花糖上的日子》)、开满水仙花的浓雾里蒙眼的新娘伸出手去摸索(《爱是什么》)……合理与不合理、荒诞与真实、抽象的非现实与具象的琐碎,在我看来,这一切与其说是舞台上的演出,不如说是一场梦境。

“世界先生的肖像”系列,2019-2020
但它并不是普通的梦。爬进窗子的彼得·潘满怀期待,可灯光大亮之时却惊愕地发现温蒂已经变成了大人。马良的作品带来的是这样的梦——巨大的粉色火烈鸟身后,是一根布满油污的排水管(《禁忌之书》)。那是一场开灯后的梦,是被时间篡改过的梦。就如同李商隐的诗: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梦境不可以重现,也不能挽留,伸出手的瞬间,一切已化为“惘然”。这份“惘然”不仅仅指的是漂浮的气球、飞舞的纸页、从镜头前划过的烟火;凝神去看的时候,你还会看到举着破烂的彩旗在荒漠里等飞机的《小旗手》,鼻青脸肿地在废墟中送信的《邮差》,少年的头上包扎着绷带,但依然第一百零一次地撑起不堪一击的翅膀(《乡愁》)……这些愚蠢的家伙都在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,正如徒然划动小圆舟的作者本身,都是朝着“永远不存在”的目标吃力地前行。这是马良作品中的荒诞与幽默,也是汹涌而来的惆怅与悲哀。观看马良造出的梦,我们仿佛拥有两双眼睛。一双沉浸梦中,看到的是温柔,是不变,是渴望的“追忆”;另一双置身事外,明白回忆早已支离破碎,再努力也只不过是缝缝补补,一切已成“惘然”。


“故境幽探图谱”系列,2017-2018
他曾经有一个装置作品,名为《用天真做印信》,窃以为,这是对他创作信念的最佳注解。引信既关键又脆弱,它是核心,是前兆,也是终结。用天真做引信,意味着他要把所有的童年,所有的回忆,所有的青春拿来做燃料。每次创作都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。马良是少有的“舍身饲虎”式的作者。从他的作品里我们能感受到巨大的矛盾,一如他的自称:“最乐观的悲观主义者”。他的悲观为作品抹上浓厚的宿命论底色,可他对世人的悲悯与温柔又让他急切地需要为人们点燃一些光亮。于是最终他选择将自身奉献出去。他将自己的不安、怯懦、渴望、孤独,毫无保留地放进作品里,将自己最私人的情感和盘托出,鲜血淋漓地摆在观者面前。一旦意识到这一点,再去看他作品中那些死去的小鸟,那些空荡荡的盔甲,以及所有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奋力演出的故事,你甚至会被那些美丽的画面刺痛。


今天之前都是昨天,2025
翻开这本画册,纵观马良的作品,我们会发现他几乎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创作方式。他似乎不懂得如何停下来。也许对马良来说,没有唯一的方法,也没有最好的方法。如果他真的有一座永无岛,那这座岛一定是时刻不停地在变化的。尽管使用的手法、呈现的视觉各有不同,但也很容易辨认出是马良的作品。因为他并非在创作画面,而是在陈述。而作为一名观者,我能强烈地体会到他的陈述已经借由画面达到了尽头,亦即,只有他创造的画面方能全然地展示出他的陈述,任何其他媒介都无法做到更好。
所以,尽管我在这里洋洋洒洒,可不过是用手指出月亮,想看到月亮本无需手指。翻开下一页,放下逻辑与理性,全然投入这场梦罢。想得到梦的精髓,惟有身处梦中。


事关生死的十四行诗,2020
自述文章
马良:永无岛
“我们都曾经去过那里,
甚至现在仍然能听到海浪声,
只是我们再也无法上岸了。”
——詹姆斯·巴里《彼得·潘》
《永无岛》汇集了我过去近二十年的摄影创作。这个标题的灵感源于詹姆斯·巴里的《彼得潘》。虽然大家可能都熟悉小飞侠的故事,但我在重读时感受到了一些独特的东西。我将这些感悟融入这本书的编辑构思中,用“永无岛”作为线索,将作品串联起来。
《西游记》

西游记,2008
《西游记》探讨的是中西方文化能否交流以及如何交流的问题。2008年奥运会期间,我在国外频繁参展,常常感到我们的作品他们其实看不懂,尽管他们带着巨大的善意试图理解。
这件作品正是对这种状况的一种调侃。我仿佛带着“中国文化”去“西游”,而观众看到的所有元素——那些来自花鸟市场、旧货商店的物件,以及我自己“捏造”的中国符号——被拼凑在一起。我在其中放置了一副对联,很多人没细看上面的意思。这副对联是用英文写成,却模仿中文瘦金体的书法,内容是:“爱东农得盎色”(I don't know the answer / 我不知道答案)和“Even I know I don't want to tell you”(即使我知道,也不想告诉你 / 也无法告诉你)。
《上海最后一个骑士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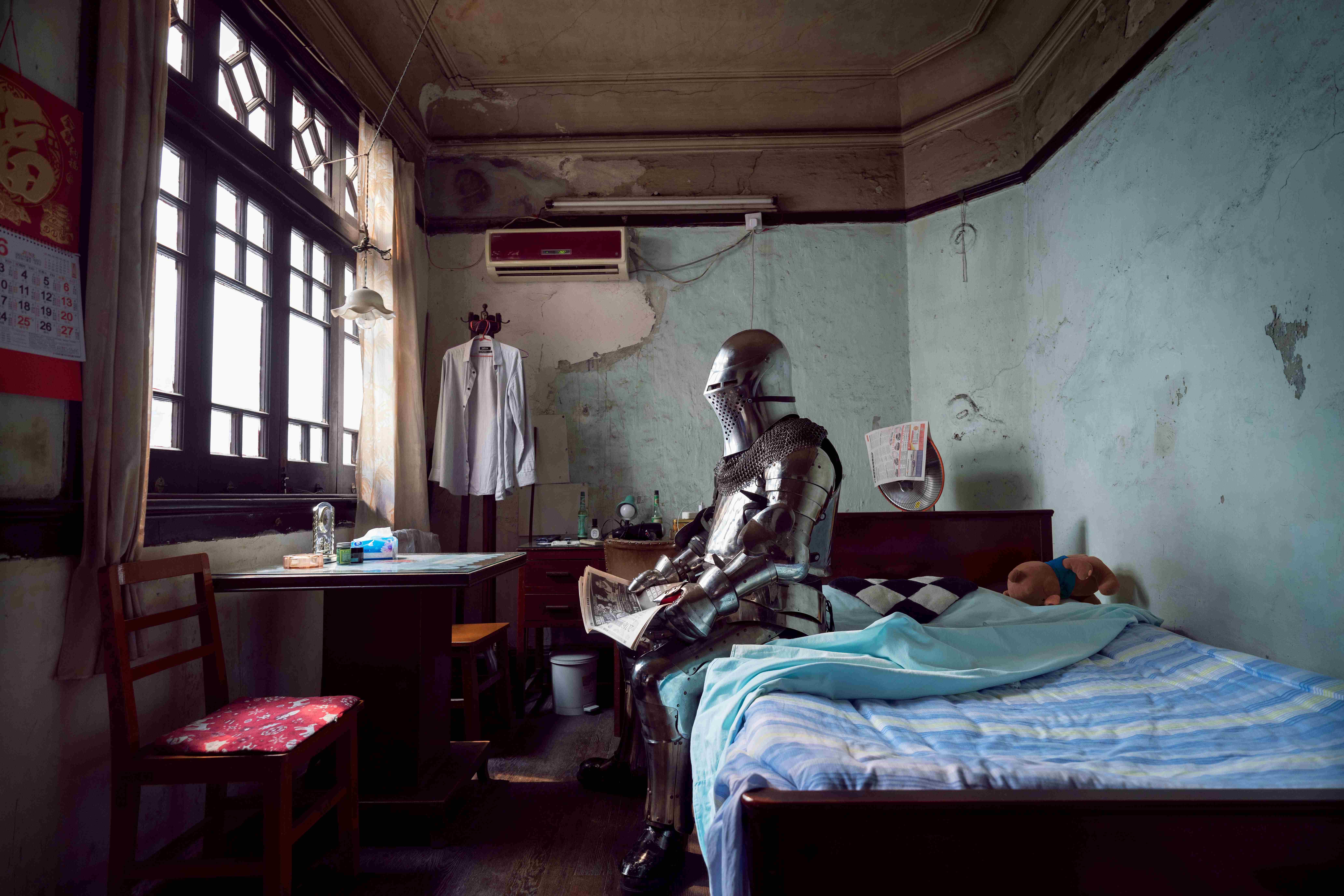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最后一个骑士,2020
《上海最后一个骑士》拍摄于2020年。我表哥家在上海有一栋漂亮的石库门老宅,2022年被拆除了。拆迁前,亲戚请我去帮他们拍些照片留念。那天我带着相机去了,一进门就觉得这场景太棒了,一定要创作一件作品。于是,我同时完成了两个任务:为家族拍摄老宅留念,以及创作这张作品。
画面中是一个人穿着盔甲坐在房间里。学过美术的朋友会认出这是典型的“维米尔光”——一扇窗,一束光线,一个安静的人物。这是件非常简洁的作品:房间里的一切陈设都保持原样,我唯一的设计就是请人穿上盔甲坐在那里。
了解我之前作品的人都知道,我惯于精心布置场景。但从这件作品开始,我放弃了这种手法。我想表达的是人与时间的对抗感——一个困在老房子里的骑士,像个困兽。他手里拿的东西并非武器,你们认识吗?
拍完后我才发现,几乎没人认得它。这是我们上海人以前晒被子时用来拍打灰尘的工具。它象征着最庸常的生活。骑士满身盔甲,手持这样一件日常器物,在房间里无所适从,形成一种强烈的张力。其实我带了非常精美的刀剑去,但拍摄时突然发现了这个拍子,觉得让他拿着它才最贴切。这些年展览时,常有年轻人询问这是何物,这种承载着生活记忆的物件,正逐渐被遗忘。
《你的样子》


你的样子,2020
《你的样子》源于一次拍摄经历,我结识了一群练习“全甲格斗”的年轻人。这是一种相对小众的体育项目:男性穿着全身定制盔甲(因为每个人身材不同,盔甲必须量身打造),手持真刀进行搏击,目标是将对方队伍全部击倒。
这项运动很有意思,我若年轻些,真想参与。参观他们的训练场地时,看到架子上摆满了头盔,这个景象深深触动了我。头盔里面本应有人,此刻却是空的,像一个躯壳。这引发了我的思考:为什么男性如此热衷于这种对抗性的运动?或许人类血液中好斗的本能始终存在。
这让我想起我的父亲,他是一位戏剧导演。他一生渴望创作一部反战作品《长平之战》,讲述一场惨烈的古代战役。在我小时候,他常对我讲:人类应当反战,应当停止互相厮杀。
《彼岸花——献给老照片里的佚名者》


彼岸花——献给老照片里的佚名者,2020
《彼岸花》的由来,是我收藏了不少老照片,其中一些是别人提供的资料。有一次,我看到一组照片,拍的是一个上海家庭,但身份已不可考。照片的艺术水准极高,不像出自普通照相馆匠人之手,我猜想拍摄者或许是位热爱摄影的父亲。他用6×6画幅相机,记录了这个家族生活的诸多片段。
其中一张照片深深打动了我:一个女孩蹲在一丛花中。那花正是彼岸花(又称曼珠沙华)。在佛教文化中,它象征着生死之间的信息,传说开在冥河两岸。女孩蹲在彼岸花丛的画面,瞬间点燃了我的创作灵感。
我想创作一件影像作品,但照片本身又是主角。用相机再拍一张照片显得很奇怪。于是,我选择用工业扫描仪来完成这件作品。这是一次性扫描完成的。
创作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:一天清晨散步,我在郊区树林里发现了一张捕鸟网,上面挂着一只死去的鸟。我拆毁了网,把鸟和网都带了回来。这张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细网,是专门用来捕杀鸟类的。我突然觉得,这只鸟象征着生命中那些无法逃脱的宿命。背景中那个方块,其实是老式大画幅相机的胶片盒(木制后背)。
我将这些元素——那些老照片(我得到的是电子版,将它们制作成实体照片,有些放大了)、彼岸花、捕鸟网和死鸟、老相机后背——布置在扫描仪上。我请了上海一位著名的花艺艺术家帮忙挑选和布置彼岸花,在扫描仪上搭建了一个宛如祭坛的场景。每次扫描大约需要15分钟,最终得到的画面极其高清:以老照片为核心,周围环绕着这些充满象征意义的物件。